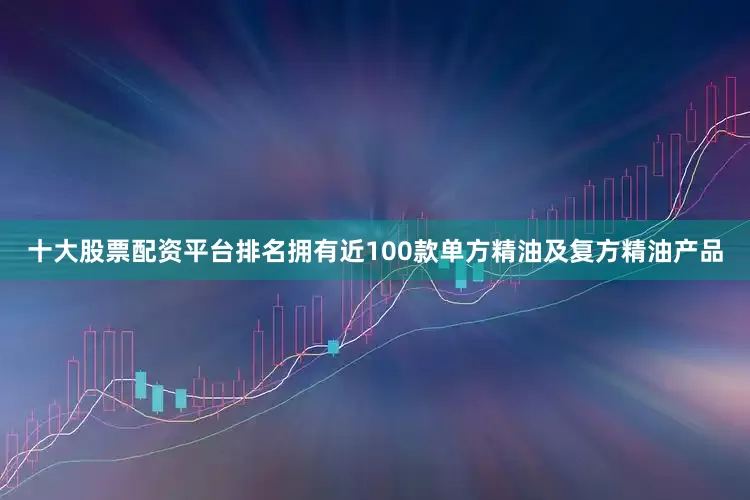“剑英同志,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,再这么下去,我们都要成历史的罪人了!”
陈云同志看着窗外萧条的景象,痛心疾首地对我说。
我何尝不是心急如焚。
“我们必须让他出来!只有他,才能让国家有希望!”

01
一九七七年初的中国,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,虽然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,但身体依然虚弱,步履蹒跚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,像一声春雷,曾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希望。人们以为,那场持续了十年的噩梦,终于结束了,好日子,就要来了。
然而,冬天,并没有那么容易过去。
北京的街头,灰蒙蒙的。人们穿着千篇一律的蓝色或灰色的衣服,表情,也大多是麻木和迷茫的。商店的橱窗里,商品少得可怜,凭票供应的牌子随处可见。买一斤肉,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;扯几尺布,要等上好几个月。
在上海的火车站,大批大批的知识青年,从农村返城。他们响应当年的号召,上山下乡,把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。可现在,他们回来了,却发现城市里,没有他们的位置。没有工作,没有住房,他们成了被遗忘的一代,前途渺茫。
在东北的工厂里,许多机器,已经停产了。工人们无事可做,每天上班就是看报、喝茶。厂里的标语还在,口号还在,但那种火红年代的生产热情,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整个国家,仿佛被一层无形的、厚厚的冰给封住了。
经济,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人心,也充满了困惑和不安。
人们都在问:打倒了“四人帮”,为什么日子还是老样子?我们的国家,到底要往哪里去?
这层冰,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,更是思想上的禁锢。
当时,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,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,被称为“两个凡是”。
那就是: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;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
这个提法,在当时有其稳定局势的考虑。但是,它也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把所有人的思想,都给牢牢地捆住了。
这意味着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所有的冤假错案,都不能平反。
这意味着,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,还要继续执行下去。
这意味着,任何新的、不同于过去的想法,都是错误的,都是对伟大领袖的背叛。
一天,一位在“文革”中受了十几年迫害的老干部,刚刚恢复了工作。他在办公室里,看到了报纸上宣传“两个凡是”的社论。
他读着读着,手开始发抖,脸涨得通红。
他猛地把报纸摔在地上,气得浑身哆嗦,对着身边的同事,低声怒吼:
“混账!这是什么逻辑!”
“照这么说,我们这十几年受的苦,都白受了?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,都白死了?”
“我们这个党,我们这个国家,就准备抱着这些错误的条条框框,一条道走到黑吗?!”
“这简直是新的个人迷信!是思想上的倒退!”
这声压抑的怒吼,道出了当时许多正直的、有良知的干部和群众心中共同的愤慨。
人们渴望变革,渴望思想的解放,渴望能有一个人站出来,带领他们,砸碎这层厚厚的冰,找到一条新的、能让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的道路。

02
虽然官方的报纸和电台,还在大力宣传着“两个凡-是”,整个社会,看上去万马齐喑。但是,在看不见的地下,一股要求变革、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潜流,正在汹涌澎湃。
这股潜流,首先来自民间。
在北京的街头巷尾,人们开始悄悄地传阅着一些手抄本。其中流传最广的,是一首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。
诗里,人们用最真挚、最悲痛的语言,怀念着敬爱的周总理。而在怀念周总理的同时,字里行间,也流露出对“四人帮”的愤恨,和对另一位老搭档——邓小平的期盼。
“欲悲闻鬼叫,我哭豺狼笑。洒泪祭雄杰,扬眉剑出鞘。”
这“扬眉剑出鞘”,扬的是什么眉?出的又是什么剑?人们都心知肚明。
除了诗歌,还有信件。
一封署名为“中共中央办公厅部分干部”的匿名信,像一颗重磅炸弹,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子弟中,悄悄地流传开来。
信写得非常大胆,也非常尖锐。
信中,公开质疑“两个凡是”的正确性,指出这是新的“个人崇拜”,是思想上的僵化。
信中,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说,却又不敢公开说出口的要求:
“我们强烈要求,让在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中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同志,重新出来工作!”
“我们不要那些空洞的教条,我们要的是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、发展经济的实干家!”
“我们相信,只有邓小平同志,才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!”
这封信,虽然无法公开发表,但它所代表的,却是一种强大的、不可遏制的民意。
这股潜流,也来自那些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。
他们中的许多人,都曾在“文革”中,和邓小平一起,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受尽了迫害。他们之间,有着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特殊情谊。
他们更清楚地知道,在一九七五年,邓小平受毛主席委托,主持中央工作时,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,曾经在短短几个月内,就让全国的局势,有了明显的好转。
他们深知邓小平的能力、魄力和手腕。
一位刚刚官复原职的老部长,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,端起酒杯,感慨万千。他说:“同志们啊,我们是活过来了。可是,国家这个样子,我们怎么能安心呢?现在这个局面,就像一盘死棋,需要一个高手,来把它盘活啊!”
另一位老将军,接过话头,一拍桌子,说道:“什么高手!我看,能下这盘棋,敢下这盘棋的,就只有一个人——小平同志!”
“对!只有他出来,我们这个国家,才有希望!”
这样的议论,这样的呼声,在北京的各个“大院”里,此起彼伏。
民心所向,大势所趋。
虽然,在公开的场合,邓小平的名字,还是一个禁忌。
但是,在亿万人民的心中,这个名字,已经等同于“希望”,等同于“变革”,等同于一个更加美好、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
03
民间的潜流在涌动,而在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最高层,几位德高望重的元老,也怀着同样沉重的心事。
他们的目光,同样聚焦在了那个住在米粮库胡同的老人身上。
第一个,是陈云。
陈云是党内公认的经济大师。他为人低调,不事张扬,但看问题,总是一针见血,直达本质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他重新开始接触经济工作。然而,当他看到一份份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数据报表时,他的心,沉到了谷底。
国民经济,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财政赤字巨大,工业生产停滞,农业连年歉收,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……每一个数字,都像一把锥子,刺痛着他的心。
一天晚上,他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同志,叫到自己的书房。
他指着桌上那一堆堆的报表,脸色凝重地说:“同志们,都看看吧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家底。可以说,比建国初期,还要困难。”
一位同志叹了口气,说:“是啊,陈云同志。‘四人帮’这十年,把我们的国家,折腾得太苦了。”
陈云摇了摇头,说:“把问题都推给‘四人帮’,是简单的。现在的问题是,打倒了他们,我们该怎么办?路,到底该怎么走?”
他又拿起一份报纸,上面还在宣传着“两个凡是”。
他用手指,敲了敲那篇文章,冷冷地说:“靠这个,能让工厂开工吗?能让农民吃饱饭吗?不能!这只会把我们的路,越走越死!”
书房里,陷入了一片沉默。
陈云看着大家,缓缓地说出了他心中藏了许久的话:
“我们现在需要的,不是抱着过去的教条不放,而是需要一个有魄力、有能力、懂经济、敢于打破常规的人,出来主持大局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,一字一顿地说:
“在我看来,现在党内,具备这样条件的人,只有一个。”
他没有说出那个名字,但在场的所有人,都心知肚明。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啊。” 陈云最后长叹一声,结束了这次谈话。
而另一位怀着同样心事的元老,是叶剑英。
作为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最高决策者之一,叶帅在党内和军中,拥有着一言九鼎的威望。他深知,国家的稳定,离不开军队的支持。
这段时间,来他西山住所拜访的老将军、老战友,络绎不绝。
他们谈论的话题,几乎都离不开一个人——邓小平。
“叶帅,”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,握着叶剑英的手,激动地说,“现在党内、军内,大家的心里,都憋着一股劲儿啊!都盼着小平同志能早点出来工作!”
另一位将军,更是直言不讳:“现在有人想搞新的‘凡是’,继续把小平同志压着。我们这些老骨头,可不答应!要是小平同志出不来,我们死不瞑目啊!”
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话,叶剑英的心里,也翻江倒海。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邓小平的才干。他也知道,只有邓小平出来,才能真正地稳定军心,凝聚党心,带领国家走出困境。
他也一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,做着各种努力。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,向华国锋建议,应该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。
然而,华国锋虽然对他言听计从,但在“两个凡是”这个根本问题上,却始终迈不开那一步。
叶剑英知道,这件事,不能再拖了。
他看着窗外萧瑟的秋景,心中暗下决心。必须想个办法,彻底打破这个僵局。
他想到了陈云。
他知道,陈云同志在党内的资历和智慧,同样举足轻重。如果他们两个人,能联起手来,形成共识,那么,这件事的分量,将完全不同。
一个掌管着“枪杆子”,一个深谙“钱袋子”。
一位是军方的定海神针,一位是经济领域的最高权威。
这两位元老的目光,不约而同地,聚焦在了一起。
他们知道,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,为了亿万人民的期盼,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

04
一个深秋的夜晚,寒意袭人。
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,悄无声息地,从北京城里,驶向了西山。车上坐着的,是陈云。
他今晚要去拜访的,是叶剑英元帅。
这是一次没有提前约定,也没有通过秘书安排的会面。两位党内最具分量的元老,都默契地选择了这种最秘密、最直接的方式。
当陈云走进叶剑英那间简朴的书房时,叶帅已经泡好了一壶热茶,在等着他了。
没有过多的寒暄,两位老战友,一见面,就直奔主题。他们的时间,都很宝贵。
“剑英同志,”陈云先开口了,他的声音,一如既往地沉稳,“国家现在这个样子,你我都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啊。”
叶剑英点了点头,叹了口气:“是啊。打倒了‘四人帮’,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。没想到,又来了个‘两个凡是’,把大家的手脚,都给捆住了。”
陈云接过话头,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这个‘凡是’,本质上,还是个人崇拜那一套。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,更不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不把这个紧箍咒给拿掉,我们国家,一步也前进不了。”
叶剑英深以为然。他看着陈云,问道:“那你我的看法,我们该怎么办?”
陈云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反问了一句:“剑英同志,你觉得,现在党内,谁站出来说话,最有分量,最能打破这个僵局?”
叶剑英笑了。他知道,陈云这是在和他“对表”。
他端起茶杯,轻轻地吹了吹热气,不紧不慢地说:“能打破这个僵局,能把这盘死棋盘活的人,我看,只有一个。就是那个四川来的‘小个子’嘛。”
两位元老,相视一笑。
虽然谁都没有直接说出那个名字,但他们心中,早已达成了高度的共识。
让邓小平复出,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。
然而,共识达成了,新的问题又来了。
怎么让他复出?
叶剑英的眉头,又锁了起来。他说:“国锋同志那边,我找他谈过好几次了。他为人忠厚,也想把国家搞好。但在小平同志复出的问题上,他顾虑重重。”
“他担心什么?”陈云问。
“他担心两件事,”叶帅伸出两根手指,
“第一,小平同志复出,会不会否定‘文革’,会不会追究‘批邓’的责任?这会动摇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。
第二,也是最根本的,就是那个‘两个凡是’。主席生前,亲自发动了‘批邓’,现在让小平复出,不就等于公开承认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吗?这个坎,他迈不过去。”
听完叶帅的分析,陈云沉默了。
他知道,叶帅说到了问题的要害。华国锋的这两个顾虑,非常现实,也非常棘手。
如果不能打消他的这两个顾虑,那么邓小平的复出,将遥遥无期。
书房里,再次陷入了沉思。
两位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的元老,为了这个国家的命运,在深夜里,绞尽脑汁。
他们就像两个最高明的棋手,面对着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。他们知道,那颗叫做“邓小平”的棋子,是整盘棋的“棋眼”。只有落下这颗子,才能激活全局。
可是,现在,这颗最关键的棋子,却被一道看似无法逾越的“理论高墙”给死死地堵住了。
“两个凡是”……
毛主席晚年的错误……
这道墙,太高,太厚了。
它像一座巨大的冰山,横亘在变革的道路上。
看着叶剑英那凝重的表情,陈云的心,也沉了下去。难道,这场关乎国家未来的破冰之旅,真的要在起点,就被彻底堵死了吗?
难道,他们这些老家伙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,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,继续滑下去吗?
夜色,越来越深。前路,似乎也越来越迷茫。

05
面对叶剑英提出的那个几乎无解的难题,陈云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。
他知道,和华国锋去硬碰硬地辩论“两个凡是”的对错,是行不通的。那会直接触及到华国锋执政合法性的根基,只会让他更加警惕和抗拒。
必须换一个思路。
必须找到一把钥匙,一把能绕开理论陷阱,又能打开华国锋心结的钥匙。
陈云的脑子,在飞速地运转着。
突然,他的眼前一亮。
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一个非常巧妙,也非常务实的办法。
他抬起头,看着一脸凝重的叶剑英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。
“剑英同志,”他缓缓开口,声音不大,却充满了自信,“我看,我们都走进了一个误区。”
“误区?”叶帅有些不解。
“对。我们总想着,要先从理论上,说服国锋同志,让他承认‘两个凡是’是错的。这条路,很难走通。”陈云解释道,“我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问题呢?我们不跟他辩论理论,我们跟他谈事实,谈结果。”
叶剑英的眼睛,也亮了起来:“哦?怎么个谈法?”
陈云端起茶杯,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,然后,说出了那句堪称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、充满政治智慧的破局之言:
“下一次,我们再找国锋同志谈。我们不要提‘两个凡是’对不对,也不要提主席晚年有没有犯错误。我们就只跟他说一句话。”
“我们就告诉他:国锋同志,现在国家经济到了什么地步,人民生活到了什么地步,你比我们都清楚。理论上的问题,我们可以先放一放,争论一百年也争论不清楚。”
“但是,让人民过上好日子,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,这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事实?是不是对主席最好的告慰?”
“现在,能做到这一点,能带领全党全国人民,实现这个目标的,大家公认,只有小平同志。让他出来,把经济搞上去了,人民满意了,拥护你了,你这个领导人的位置,不就坐得更稳了吗?”
“至于那些理论问题,让事实来说话。事实,比任何解释,都更有力量。”
这番话说完,书房里,一片寂静。
叶剑英愣住了。他反复咀嚼着陈云的这番话,越想,眼睛越亮,越想,越觉得高明!
太高明了!
陈云的这番话,完全避开了“对与错”的理论纠缠,直击问题的核心——那就是“利弊”。
叶剑英猛地一拍大腿,哈哈大笑起来:“高!陈云同志,你这一招,实在是高!釜底抽薪啊!”
“这就叫‘不争论’,”陈云微笑着说,“先把事情做了,让大家看到好处。等到木已成舟,那些理论上的问题,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”
几天后,陈云和叶剑英,再次联袂找到了华国锋。
他们完全按照之前商量好的策略,不再和华国锋纠缠于“两个凡是”的理论问题,而是把国家经济的困难,人民生活的疾苦,掰开了,揉碎了,摆在他的面前。
然后,他们把那套“不争论,先做事,看结果”的逻辑,向华国锋和盘托出。
华国锋听完,沉默了。
他不得不承认,陈云的这番话,说到了他的心坎里。他确实为国家的经济状况,愁得焦头烂额。他也确实需要一个能干的、有威望的人,来帮他分担压力,打开局面。

06
华国锋的态度虽然松动了,但要让邓小平正式复出,还需要一个契机。
时间来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,一件看似不起眼,却在中国现代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大事发生了。
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,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
第二天,这篇文章,被《光明日报》以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的名义,公开发表。随后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等中央级媒体,纷纷转载。
这篇文章的观点,在今天看来,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。
但是,在那个年代,它的发表,不啻于一声惊天动地、振聋发聩的春雷!
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它在告诉所有的人:任何理论,任何指示,包括领袖的决策,到底是对是错,不能看它是谁说的,不能靠本本主义,而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。实践证明是对的,我们就要坚持;实践证明是错的,我们就必须修正。
这篇文章一发表,立刻在全国范围内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一场关于“真理标准问题”的大讨论,在全国范围内,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
保守派们,如遭雷击。他们立刻组织文章,进行反驳和批判。他们指责这篇文章,是“砍旗”,是“非毛化”,是“典型的修正主义”。
一时间,报纸上,会议上,充满了激烈的争论。
然而,他们低估了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的渴望。
这篇文章,说出了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,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。它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人们思想的闸门。
全国绝大多数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领导人,纷纷表态,支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这一观点。
各大高校的学者,工厂的理论骨干,农村的基层干部,都加入了这场大讨论。
思想的坚冰,在这场大讨论中,被彻底地炸开了!
而这场大讨论背后,最重要的支持者,正是那些渴望变革的元老们。
陈云、叶剑英,以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,都旗帜鲜明地,站在了“实践派”这一边。
更重要的是,远在南方休养的邓小平,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,他敏锐地意识到,这,就是他复出的最好契机,也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理论基石。
他立刻表态,高度赞扬了这篇文章,认为“这篇文章,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,都说清楚了”。
有了邓小平的表态,有了绝大多数党内元老和地方领导的支持,这场大讨论的胜负,已经毫无悬念。
“两个凡是”的理论基础,被彻底动摇了。
它就像一堵看似坚不可摧的墙,在“实践”这台强大的推土机面前,轰然倒塌。
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,扫清了最后、也是最根本的理论障碍。
那一天,北京的天空,格外晴朗。
一位普通的市民,在报纸上读完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道后,激动地对家人说:“天,要亮了!”
是的,天,真的要亮了。
那一声思想解放的春雷,已经炸响。
一个崭新的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,即将在它的催生下,破土而出。

07
随着“真理标准问题”大讨论的深入,“两个凡是”的枷锁被打破,邓小平复出的呼声,也从地下的潜流,变成了公开的、势不可挡的浪潮。
人民,不再满足于私下里的议论和期盼。
他们开始用各种方式,表达着他们对这位老人的支持和期待。
在北京,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,又开始有群众自发地,送来花圈。这些花圈,名义上是悼念周总理,但许多花圈的挽联上,都写着一些意有所指的诗句。
“总理与小平,肝胆相照,力挽狂澜。”
“盼小平,拨乱反正,重整河山。”
这些朴素的语言,代表了最真实的人心向背。
在军队里,这种期待,表现得更加直接。
许多高级将领,公开上书中央,请求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。他们说:“军队,需要一个有魄力、懂军事的统帅。小平同志,是众望所归。”
在知识界,更是掀起了一股“邓小平热”。
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,回顾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主持整顿时的功绩。他们用事实证明,邓小平是一位有能力、有办法,能迅速扭转困难局面的卓越领导人。
这一切,都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、不可抗拒的政治压力,推动着历史的车轮,滚滚向前。
面对这样的形势,华国锋知道,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,再阻止邓小平的复出了。
顺应民意,顺应大势,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很快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正式做出了为邓小平平反、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。
这个消息,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,但已经通过各种渠道,迅速地传遍了全国。
整个中国,都沸腾了!
人们奔走相告,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在上海的工厂里,当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时,停产许久的机器,自发地,重新轰鸣了起来。一位老师傅,激动地抹着眼泪说:“我就知道,有他在,我们这厂子,就有救了!”
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,几个胆大的农民,在悄悄地搞“大包干”。他们听到这个消息,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带头的那个农民说:“小平同志出来了,他最实事求是,肯定会支持我们这么干!大家放心大胆地干吧,好日子,就要来了!”
在大学的校园里,刚刚通过恢复后的高考,走进课堂的学子们,欢欣鼓舞。他们知道,这位老人,最重视知识,最尊重人才。一个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,即将来临。
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期待。
因为,邓小平这个名字,在当时,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。
他代表着一种精神——实事求是,打破禁锢。
他代表着一种希望——改革弊政,发展经济。
他代表着一个承诺——让这个国家,告别贫穷和动荡,走向富强和稳定。
人民的期待,已经汇聚成了汪洋大海。
而那位承载着亿万人民期待的老人,也即将结束他“三起三落”政治生涯中,重新走上历史的舞台。

08
一九七七年七月,北京。
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,在京西宾馆隆重召开。
这次会议,将正式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程序。
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,就是通过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》。
当会议主持人,宣布这项决议,并提请全体委员表决时,会场里,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。这掌声,经久不息,代表了全党共同的心声。
决议,被全体一致通过。
这意味着,邓小平,这位在政治风浪中“三起三落”的传奇人物,终于,又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回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。
消息传出,举国欢腾。
然而,故事的主角,邓小平本人,却显得异常平静。
在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,他没有去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,也没有去炫耀自己的胜利。
他只是淡淡地说:“我出来工作,可以做一点事……我感谢党,感谢同志们。”
他还说:“我们党的最好的传统,就是实事求是。毛主席,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,就是毛泽东思想。毛泽东思想的精髓,就是实事求是。”
他用最平实的话语,为未来的变革,定下了最重要的思想基调。
会议结束后,一辆普通的红旗轿车,驶离了京西宾馆,向着北京城的中心驶去。
车子,路过天安门广场。
车窗缓缓地摇下。
车里坐着的,正是邓小平。
他望着窗外,那熟悉的、却又仿佛有些陌生的城市。他看到了广场上,那些洋溢着笑容的、充满期待的年轻人的脸。
他没有说话。
他的脸上,也没有太多的表情。
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睛里,闪烁着光芒。
车子,继续前行。
宝尚配资-网上配资炒股平台-十大股票配资平台排名-个人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